作家刘亮程曾在作品《一个人的村庄》里说:落在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冬。不过对于同性恋群体而言,这并非是个体的孤独过冬,而是一个群体的漫漫长夜。
无法被世俗主流认可的孤独落寞,成为长期悬在同性恋群体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为了能够保守住自己是同性恋的秘密,屠龙的少年最终化身为新的恶龙,80%的男同性恋者选择了结婚,并由此衍生出了另一个隐秘的特殊群体——同妻。
事实上,主流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包容度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同性恋群体的话语权也正在得到保障和扩大;但另一方面,同妻群体的曝光量却仍然微乎其微,她们就像是被遗忘在资讯海洋的某个孤岛之上,一边继续在名存实亡的空壳人生里煎熬,一边又无人可以说起、更无从说起。
骗婚、家暴、艾滋病、生育机器、无性婚姻,种种悲剧的背后,是1600万人的失语。
认知偏差的原因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真相了解甚少,接下来公布的一些权威专家的数据也许会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著名的性学家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指出,我国同性恋者占总人数的3%~4%,换言之大概是在4000万人的规模;
而“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的张北川教授对于男同性恋者预估数据也有2000万人,而在这之中大概有80%的男同性恋会因为种种原因而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而步入婚姻娶妻生子。换言之,我国的同妻人群数量至少在1600万人。
如此庞大的规模人群所获得的社会曝光量,和男同群体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国内最大的网络社区聚集地,百度贴吧中gay吧的关注人数为541万,累计发帖量3亿;而同妻吧的关注人数仅有4万,累计发帖量71万。
男同群体的网络社区并不仅仅只有gay吧一个而已,这一群体寻找归属感和网络发声的平台远比普通人所认为的要多得多,但同妻群体无论是在主流舆论的曝光量,还是在用于互助宣传的网络平台,都远不如前者。
这个社会对于男同群体的包容度还不够,而与此同时,男同群体内心还有强烈的生育欲望,这两个原因让绝大多数男同选择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取向和女性结婚。
“有妻子的已婚男“——这一身份是男同群体用于应对周围冷眼最好的挡箭牌,也满足了自己和父母想要后继有人的梦想。
找异性结婚对于男同来说,似乎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选择,但这里唯一被牺牲的对象是那个毫不知情,以为自己找到真爱的同妻。
没有爱情做基础的婚姻注定一地鸡毛。从哈工大社会人类学研究小组在2015年公布的跟踪调查报告结果来看,几乎九成同妻都遭遇过家暴,三成同妻没有性生活,但最终也只有三成同妻选择了离婚。这些残酷数据的背后,都是1600万同妻的空壳婚姻生活。
“就像是在机场等一艘船,又像是暗无天日的无期徒刑。”当我采访一个同妻时,她平复了很久,然后说出了这句话。骗婚是造成1600万同妻悲剧人生的原罪,但骗婚的情况并不少见。
就在上个月,一个揭露gay男友骗婚的帖子在网上疯传,如果不是女生无意中看到了对象的手机,她不会想到自己谈婚论嫁的高冷男友居然在外面甜蜜地叫着别人老公,甚至他还心思缜密地跟同性爱人商量着如何在婚后一步步骗婚生子,再夺走财产,让女生净身出户。
不难想象,如果不是被无意中被发现,帖子的原主人也将沦入这场名存实亡的空壳婚姻,在痛苦和煎熬中耗尽自己最美好的年华。
不过,骗婚对于同妻来说,只不过是悲剧的开始。这场从一开始就是以欺骗企图来结合的婚姻,注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和解,只会随着时间而变成死结。
2012年6月15日凌晨三点,四川大学教师罗洪玲在她的个人空间里留下了最后一句遗言:
这个世界真叫人疲倦,那么就让一切都结束吧!
罗洪玲的死之所以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是因为她的身份很特殊——同妻,一个1600万隐秘受害者群体之一,罗洪玲的死也在短暂时间里让公众舆论关注到了“同妻”群体。
在罗洪玲自杀前的25天,她从丈夫的手机里看到了大量不堪入目的同性聊天记录和同性交友软件,在震惊和绝望中,罗洪玲看着平静的丈夫亲口承认了自己是同性恋。
“罗老师,对不起,我就是个gay。是我骗了你,骗婚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自己。”
在罗洪玲跳楼的前一天,丈夫程建平在微博上公开道歉的这句话,成为彻底击碎罗洪玲内心所有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次日凌晨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罗洪玲用了最极端的方式来回应丈夫的欺骗,而除了她之外的绝大多数同妻仍然隐没在同性恋群体的背影里默然失语。
在张北川教授的调研中,同妻所面对的问题还远远不只家暴而已,有30%的同妻因为丈夫出去约的恶习而感染了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各种性传播疾病,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性恋丈夫被妻子发现秘密的原因之一。
在我所接触的同妻中,不少人曾因为自己的丈夫而感染性病,刘艳(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她至今都记得自己去医院看病时所受到的冷眼和鄙夷,所有人都像是躲着瘟神一样躲着自己,当医生问她是不是存在多个性伴侣的情况的时候,刘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一遍又一遍确认医生的检测报告,直到医生肯定地跟她讲:“确实是梅毒和尖锐湿疣。”
“是不是日常接触传播?”刘艳还是没有怀疑到丈夫身上,然后医生说了一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性传播,这些病需要两个人一起来治,你也得问问你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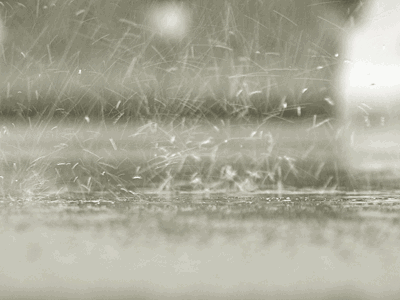
医生没有再多说什么,直到刘艳偷偷翻了丈夫的手机,一切平日里奇怪的举动都得到了解答: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其实是个同性恋。
不让翻手机,说要有个人空间;不主动发生关系,说自己工作累;总是跟同性朋友出去玩,说是为了社交圈……“我此生只有你一个女人。”结婚当天丈夫说的话,成了偌大的讽刺,刘艳确实是他唯一的女人,唯一一个不得已才拥有的女人。
但和另一些人相比,刘艳是幸运的,因为她没有感染上艾滋这样难以治愈的性病,在她选择离婚后的若干年,她会渐渐将这段回忆封存心底,并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但那些因为同性恋丈夫而感染上艾滋,或者发现丈夫是同性恋后,仍然因为生活或者孩子的缘故而不愿意离婚的同妻们,她们的地狱人生还远没有结束。
在张北川教授的调研里甚至出现了60多岁还是处女的案例,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守活寡式的婚姻在同妻群体中并不少见:算准排卵期发生关系,一旦发现怀孕后就再也不碰妻子;推说工作累,自身生理缺陷等等拒绝进行正常夫妻生活……
但比这些更可恶的,是同性恋丈夫的羞辱!当同妻对性有渴望的时候,不愿意配合的同性恋丈夫们会说出诛心的话:“你怎么这么饥渴?能不能矜持点?能不能不要像个……?”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婚姻里的PUA让女性渐渐怀疑自我,从而产生了对自我主体的羞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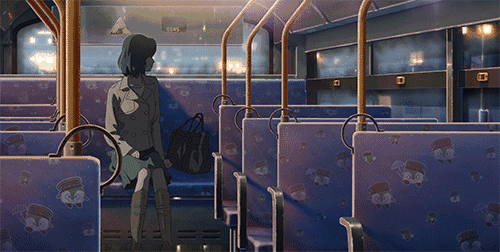
就像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何式凝在自我传记《我係何式凝,今年五十五歲》中第一章里写的那样,当她看到同性恋的男友对自己女性的身体本能抗拒时,这种羞辱感想让她从十五楼的酒店房间跳下去:
我为了拥有一个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的女性躯体而感到异常羞愧。
同妻的绝望感还并非只是来自这段无期徒刑式的无性婚姻,还来自于双方的父母和孩子。就像是当刘艳哭着告诉父母,丈夫是同性恋的时候,她的母亲反问的一句话却是:是不是你把他逼得太狠了?让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了?
刘艳没有跟生下孩子,但被骗婚而生下孩子的同妻比比皆是,当她们这类人在发现丈夫是同性恋而要绝望离婚的时候,那个无辜出生的孩子,又有谁该为他们的人生负责呢?
对于骗婚同性恋者的愤慨也并不只来源于同妻群体,就算是在同性恋群体中这类人也如同过街老鼠:“一边在圈内约,一边享受着所谓的‘正常人’的生活,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大众对于我们这类群体的反感和排斥。”
当有同性恋的圈内人在听完刘艳的故事后,代她的丈夫向她道歉的时候,一直情绪激动的刘艳平静了下来,她看着面前这些年轻相爱的同性恋者,认真地说道:
“我们同妻群体其实并不歧视同性恋,但同性之爱不应该建立在牺牲他人人生的基础上,如果可以的话,在你们被爱的同时,我们也想得到纯粹的爱情。我也希望当人生的大雪真的来临时,每个人都能在心爱之人的陪伴下温存度过那个寒冷的冬夜。”

突然想起那部在2018年获得数项金马奖提名的中国台湾电影《谁先爱上他的》,在电影的最后,曾因发现自己是同妻而抑郁的女主刘三莲,最终还是和叛逆的儿子,以及亡夫宋正远的同性恋人阿杰达成了和解。

就像是宋正远在给儿子留的遗书里写的那样:我一直认为恨才能让我们找到坚强的勇气,但有个人告诉我,爱才能让我们活得坦坦荡荡。
在采访的最后,我问刘艳有没有什么话要为同妻群体发声的?
刘艳思考了很久,然后在她离婚纪念日的当天,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不要忘记社会深处那个被紧闭的柜子,更不要忘记被那柜子的阴影所挡住的女人们。希望那些被尘封在柜子里的人们可以在阳光下大声说爱,也希望那些曾被阴影遮住的女人们能重新沐浴阳光。
风雨之后,必有彩虹;彩虹之外,晴空万里。







